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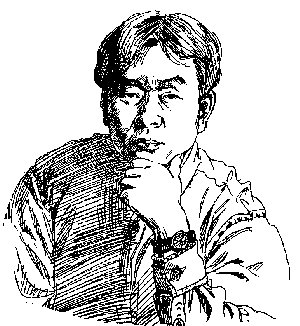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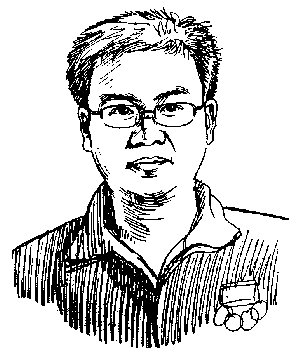
作为大学教育的“最后一课”,师长的毕业演讲一直倍受关注。继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()校长李培根的“根叔体”演讲引发轰动后,许多演讲者开始走“亲民路线”。今年,许多狂飙网语、流行语的毕业演讲更是赚尽眼球,关于其的争议也在媒体的持续炒作中不断扩散开来。本期,我们特约三位观察员共同探讨大学毕业演讲应有的价值追求。
“最后一课”更应守护大学价值立场
范玉刚
喧嚣的2012年大学毕业季在淡去,但毕业演讲刮起的“潮风”依然劲吹,其声势之猛、色彩之艳、流行之快,想让人不闻不问都不可能。
作为一道必不可少的“文化大餐”和刻骨铭心的生命仪式,大学毕业典礼浓缩了大学生活的精彩、五味杂陈和社会期许。作为“告别礼”,它既度量了大学文化的“体温”,又回应了社会的关切,还杂糅了相互激荡的文化思潮。“最后一课”的毕业演讲,无论是语重心长,娓娓道来,还是“给力”的网络潮语,一定意义上,都显现了时代、大学以及社会大众的期望。在这极富象征意味的人生仪式上,毕业演讲固不应板着面孔说教,但更不该媚态式地追随网络潮语。
当前,毕业演讲“搏出位”已成为毕业季的一道风景。一些因网络流行语而走红的毕业演讲,在赢得某些人喝彩时,也令一些人感觉很“伤不起”。其实,毕业演讲不在于是否用潮语,而在于能否用得恰到好处。言为心声,只要演讲言之有物、言之有情,贴近学生,个性化表达,能够体现大学精神和使命,有思想、有内涵,不在乎用什么语言和表达方式。
毕业演讲融入网络潮语是对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化的回应,是对此前成为套路的毕业演讲的纠偏,但谨防过犹不及,为新潮而哗众取宠。当下争议的焦点,恰恰在于对度的把握。细思量,只有那些语重心长、浸润灵魂的亲切话语才能走入人心、打动人心,这样的演讲才有话语的力量。比如近年来“根叔体”演讲的受追捧,离不开文字背后深刻的人生哲理和文化底蕴作支撑,它不是脱离大地的“话语漂浮”,而是有着明确的价值坚守和人生导向。
大学是理想的守护者,是先进文化的引导者,大学生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,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践行者。遥想当年西南联大,一群衣衫褴褛的知识分子屹立于天地间这是国人心中的大学形象。大学毕业演讲是以演讲形式对这种形象再定格。在典礼上以价值担当意识对大学生进行人生启悟,是许多大学师长在毕业演讲中体现的价值诉求。尤其是北大1984级毕业生卢新宁,在该校2012届中文系毕业演讲上体现的价值诉求在这个怀疑的时代,我们依然需要信仰。
大学文化应引领社会潮流,以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为使命担当,而不是以矮化、滑稽化、闹剧式来追捧时潮。大学固不能脱离社会封闭自己,但在眼花缭乱的社会众生态中,也要保持应有的定力。作为人生庄重一刻的话语表演,毕业演讲可以轻松、幽默、诙谐,可以与时俱进,可以很“标新立异”,不是不能使用网络潮语,而是不能让词语空洞化、肤浅化,不能本末倒置,以网络潮语来邀宠、混淆视听,不能缺失价值担当,尤其不能迷失大学应守护的价值立场。
庄严的仪式拒绝戏说与恶搞
陈宝泉
刚过去的毕业季,江南某大学法学院毕业典礼上教师代表的“甄 体”雷人发言让笔者很开眼:毕业典礼还可以这么搞?联想起偶尔在高校看到,有穿着背心、短裙、拖鞋,罩上礼袍就去参加授学位仪式,有的还拎着学位帽,那感觉真是斯文扫地。
学校在开学、毕业时举行典礼,以体现师生对于知识、文化传承的景仰,师生间的敬爱,各自的责任,这在文明社会是百十年甚至数百年不变的程式。邻国日本的小学典礼很讲究。毕业典礼程序是,低年级学生先坐好,家长也入席,然后毕业生在班主任带领下列队入场;校长、师生代表、学区官员代表诚恳发言;毕业生列队离场时,全体起立鼓掌欢送。当天,从礼堂到校门的路都被花朵精心装饰,场景令人难忘。去年日本遭逢大地震,灾区小学师生都有伤亡,校舍倒塌。危难时刻学校依然组织庄严肃穆的毕业典礼,幸存者相拥泪别,十分感人。
仪式庄严是世界上各民族都有的文化,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珍视、敬畏与尊崇。在我国的传统中,礼制曾被认为“悠悠万事,唯此为大”。苏联解体后,俄罗斯民族许多传统没变,莫斯科的新人结婚仍然要到“无名烈士墓”献上鲜花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国外传入的大学毕业典礼仪式,其内容并非不可以调整,但不可以拿来恶搞、戏弄。
这些年,大学毕业典礼上有的校长讲话缀满网络新词已显不妥,有的教师代表油腔滑调地调侃母校,更让仪式庄严荡然无存。这些举动也许能迎合一些看动画片长大,经历应试教育重压却总也玩不够的学生的趣味,但如此轻佻、媚俗是否真有必要?即使是“脱口秀”也要有一定之规,大学教师的即兴发挥要看场合,别在讲台上信口开河。
网友对演讲者动辄奉上“某叔”、“某哥”的昵称,亲热之余,也让人品出点动作片里市井江湖的味道。这里引出一个话题:大学的师生关系。有学者说,平时师生们交流,都觉得称师长为老师最合适,这一称呼很可贵。师生之间有大爱,但是这种爱讲理性、有分寸。师长不是老板,也不是某叔、某哥。
尽管社会转型期会有信仰缺失甚至礼崩乐坏,但大学不能随波逐流。毕业典礼仪式映射大学文化,发言彰显大学水平。大学自由是指学术自由、观点自由与规章制度允许的选择自由,而不是不讲是非、缺乏理想责任、没有文化的自由。大学的典礼不能没有崇高,谁发言,讲什么都要斟酌。有学者谈到,国外一所大学的百年庆典上,校长讲的是学校百年来的业绩,而一位来自世界名校的代表讲的是百年后大学该是什么样,教育者应该作何准备。两者水平高下,听众了然于心,而我们又该从中悟到些什么呢?
可以轻松不可轻浮 可以通俗不可低俗
王亮
每到毕业季,各高校时尚、新潮的毕业典礼演讲总能引起舆论关注和网民热议。一些调侃式的表达不仅成为点击率颇高的段子,也让演讲人迅速成为网络红人。
对于越来越多的类似毕业典礼演讲,有人津津乐道,也有人忧心忡忡。人们臧否的焦点不在内容而在表达形式原本严肃庄重的毕业典礼,能不能通俗化表达和娱乐化呈现?今年流行的诸多毕业演讲稿,其实内容都传递着积极的因子和主流的价值,比如感恩母校、珍惜情谊、坚持信仰、努力奋斗,但表达上却有雅俗之别和高下之分。
在毕业这个特殊时期,在毕业典礼这个特殊场合,针对大学毕业生特殊人群,我们可否来点特别的表达?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根据美国在二战中的实证研究,按照传播学理论,谁把受众当成一触即倒的“靶子”,自说自话,定会失去受众;相反,谁能研究受众的特点,依据他们的需求,走进他们、贴近他们,定会赢得受众。
毕业典礼演讲承载着育人功能,有人将之比喻为“最后一课”,这一课时间最短,却浓缩着4年大学课程的精华,包括做人的道理与做事的方法。因而,毕业演讲除了考虑说什么,更要考虑怎么说,板着面孔、端着架子、一味说教不仅索然无味,也显然不能赢得毕业生。过去,大学思政教育难以入脑入心,失误之一就是很少花工夫去研究学生的特点和需求,并用有效的方法走进他们的心灵。对于“90后”毕业生,我们要看到其有追求、有责任、有创造的一面,也要看到其有个性、爱自由、追时尚一面。从这个角度说,毕业典礼演讲从高雅走向通俗,从教育走向娱乐,或许矫枉过正,但仍然是我们从大学生特点出发构建新型育人体系中的一个新尝试。
毕业典礼的场合,既具有公共性,也具有私密性。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特殊,感情是如此浓厚,老师、家人、兄长、导师,多重身份交织在一起。因而在笔者看来,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有点“悄悄话”的味道,像父母跟子女唠叨、师傅对徒弟叮嘱,因而对于媒体,要从善意和宽容出发去正确解读。
需要提醒高校的是,毕业典礼上的演讲要把握好度,不要让笑声代替了思考,让愚乐取代了娱乐。很多人提倡“重心往下”,但要知道,通俗往下一点是庸俗,再往下一点就是低俗。娱乐也好、通俗也罢,目的都是要以轻松、易接受的形式寓教于乐,为价值和文化的传播开启更广阔的通道。
我们需要思考的地方在于,如果把一切都泛娱乐化,主流价值得不到传播、美好情感得不到传递、育人功能得不到体现,我们得到了什么,又失去了什么?可以肯定的是,当娱乐蔓延为愚乐,它会消解文化精神的坚韧与厚重,消解主流价值的积极意义。
2012年高校毕业演讲摘录
【叮咛体】
人生的远方,不完全在于你能挣多少钱,有多大的权,成多大的名。你们之间的多数人未必能在钱、权、名方面走得多远,但你们却可以抵达心灵的远方。
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李培根
【“甄 体”】
朕私下想,诸位书生必是极好的。众爱卿均是高帅富,众爱妃均是白富美。但是,请你们记住:法律只评价客观行为,而不关心主体形象。
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副教授 高艳东
【问答体】
当你看到老人在马路上跌倒、儿童在河边落水时,你能毫不迟疑出手相助吗?当你成为一名()时,你能运用手中的权力,为素不相识的普通百姓服好务吗?当你遇到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时,你能像“最美女教师”张丽莉、“最美司机”吴斌那样舍身救他人吗?
中南大学校长 张尧学
